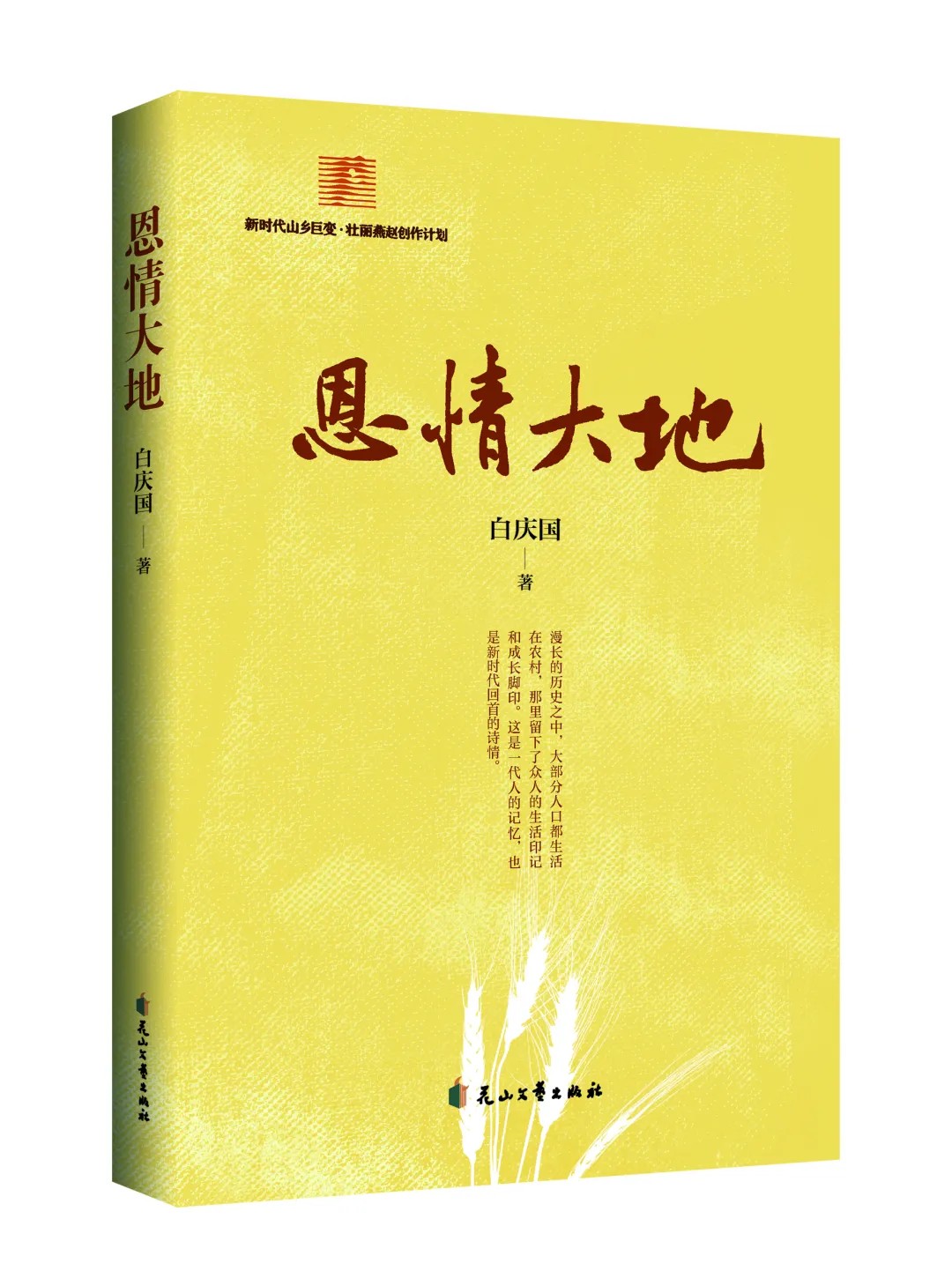在河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一位从田间地头走来的诗人——白庆国。他是农民,也是作家,双重身份在他身上完美融合,构成了他独特的创作底色。 白庆国,石家庄新乐人,坚持写诗三十多年,曾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农民诗人”,获首届郭沫若诗歌奖、第十二届河北文艺振兴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继《乡村底色》之后,白庆国的散文新作《恩情大地》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恩情大地》是一部写给村庄的深情之书,一曲唱给故乡的动人赞歌,书中记录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现在,平原上一座村庄里农民生活逐步改善的过程和细节。白庆国用细腻而质朴的笔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记忆深处的门,带我们感受乡村的脉动,聆听岁月的回响。 白庆国在书中详细描绘了乡村四季的风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温情的乡村世界。春天,万物复苏,忙碌的鸟儿穿梭于嫩绿的枝丫间搭建巢穴,为孕育新生命努力着;夏天,麦子进行最后的冲刺,大地一片金黄,人们早早起床,为麦子进行末次灌溉;秋天,天气逐渐变得凉爽,村庄里没有闲人,人们都在与秋风赛跑,把成熟的谷物和果实运回村庄;冬天,村庄披上银装,静谧而安详。 白庆国拍摄的秋日村庄 在书中,白庆国还对童年趣事进行了生动再现:捉耗子时沿着耗子洞的“窗户”挖下去,有一次竟然在耗子洞里挖到七八斤黄豆;把一块块新鲜的红薯用烧红的土块依偎起来,过上两三个钟头,就能吃上又香又甜的焖红薯……这些充满童真童趣的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童年的快乐时光,也勾起了我们对童年的无限怀念。 故乡的亲人和村庄里的生活,更是本书浓墨重彩描绘的部分。母亲烙的饼,色泽金黄、层次分明、香喷喷的,那是记忆中永远无法忘怀的味道。每一口咬下去,都能感受到母亲的爱与家庭的温暖。舅舅特别爱惜东西,衣服鞋帽旧了、破了也舍不得扔,那是老一辈人勤俭节约的美德。他们经历过艰苦的岁月,深知生活的不易,所以倍加珍惜每一件物品。在村里看露天电影、用辘轳水井里打水、用碌碡压场,用擦子把即将耕种的土地弄平……这些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如今已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作者用文字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仿佛按下时光的快门,将这些昔日农村的生活画面永远定格。 白庆国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修饰,有的只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以及对故乡亲人真挚的情。他用文字为我们保存了乡村的记忆,让没有经历过乡村生活的人,也能感受到乡村的脉搏。让我们翻开这本书,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回望来时的路,感受那份来自乡村的温暖与力量。 精彩书摘 我的作家梦 小时候,我梦想当一名作家。每当在课本上读到那些优美的篇章,就感到作家真了不起,用朴素的文字,砌起感人的故事,使读者时而大哭落泪,时而仰天咯笑。作家用文字的魔方引领读者,走进人的灵魂深处,探讨灵魂的洁白与丑恶。作家美丽的光环时时映照在我的头顶,让我有了一个美好的梦想。 然而我的作家梦奋斗了几十年,我的文学坎坷路是这样走过来的。 由于立志当一名作家,就向往多读书,然而那个时期能够读到的书很少,后来在邻居家看到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本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书籍,由于太喜欢,我读了三遍。 第一次读的时候把铁锅烧红了。第二次读的时候把我们家的驴丢了。第三次读的时候差一点儿被轧场的拖拉机碾住。我父亲特别讨厌我读书,他不想让我有任何作为,只想让我识几个字,回家当农民就行。他只要一看见我的书就撕掉,一边撕一边嚷叫,像疯了一样。我一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就决定从此再也不想当作家了。可是一接触到那些文学书籍,作家梦就又来了,想甩也甩不掉。为了这事我与父亲大吵了一顿。我父亲为了臊我的脸,把我拉到街上,当着很多人的面说,你们瞧瞧,他这个样子还想当作家。父亲的话真是刻薄到了极点,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指责我,让我简直无地自容。一些人露出鄙视的目光,一些人故意问,作家是什么色的人。父亲拍着屁股跺着脚的样子,我记忆犹新。由于伤心从此我再也没有与父亲吵嘴,父亲也不容易,我们弟兄四个,我是老大。我应该为父亲着想,帮助父亲把我们家的日子过好。为了帮助家里增加经济收入(那时,我弟弟有人介绍对象,需要一台缝纫机,根本没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在别人眼里是不正常的人),我跟着一个建筑队到北京打工了,暂时忘记了作家梦,作家梦即使出现,我也得把它按在生活的脚下,我与其他人一样吃苦流汗,把挣下的工钱如数寄给父亲。那一年我弟弟结了婚,结婚时我还在北京努力挣钱,后来我辗转到郑州打工了。 作家梦的又一次强烈出现是我在一家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总共才八百字。是我妹妹告诉我的,邮局的先生站在我家的门前喊一个叫废铁的名字,我父亲急了,我父亲冲着邮递员大发雷霆,你是不是精神病,还好我妹妹站在我父亲的身后,我妹妹说废铁就是我哥哥的笔名。我妹妹从投递员手里接过报纸,欣喜地把我的文章让我父亲看,我父亲根本不感兴趣,他把邮递员撵走了,还说以后再有这样的名字出现,不准在我家门前喊叫。我父亲可能自尊心太强了,废铁是一个烂名字没有讲究简直丢死人。 我妹妹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我,我一听就高兴地蹦了起来,我的同行认为我得了精神病。我的作家梦又一次点燃了,我用打工的钱,在郑州的新华书店买了好多书,国外的、国内的足以让我看半年。那年麦收我没有回家,我父亲一直写信催促要钱,说我三弟要学费。我一直没有回信,我假装自己失踪了。我还告诉别人如果有长相像我一样的人来找我就说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人。那一年真痛快,我在上班之余一口气读了一百本世界名著。我突然觉得我距离作家这个目标很近了,可是我仅仅发表了一篇八百字的小文章。 正当我发奋要写一个长篇的东西时,我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知所措,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我父亲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废铁”,我父亲很文雅地称呼我,我还以为父亲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紧接着父亲眉头紧锁,你小子跑到地狱我也能找到你,你三弟再不交学费就要被学校开除了,给你写了好几封信你也不回,你他x把你老子忘了。我父亲踢了我一脚,同时也踢飞了我手里的那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心疼地看着《老人与海》飞过砂浆机落在蓄水的大池子里,不一会儿沉没了。我的目光还在那里看,我父亲又说话了,赶快收拾东西跟我回家,家里的麦子还在地里长着,别人家都收割完了。我真纳闷儿,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母亲也能顶半个人,怎么麦子还没收割完?我跟着父亲坐着一列慢车回家,路上我一言未发。快到家时,父亲说你母亲突然得了脑出血,我们照顾她了,所以麦子至今没有收完。我一听说母亲得了脑出血,头要爆炸似的,我简直不相信,我母亲平时身体很好。 回家以后,母亲的确不能说话了,看见我不停地掉眼泪,我也落下了眼泪。我没有休息就跟着父亲到地里拉麦子。兄弟和妹妹早把我家七亩地的麦子割倒了,专等我回来收拾。 跟我装车去。父亲很冷地说了一遍,就举起驴鞭子向驴的屁股扬去。父亲的驴鞭是根竹棍,父亲扬了一下,驴就走了起来。趁驴还没走远,我折回厨房,喝了一大瓢凉水,这时我才觉得有了点儿精神。我跟在父亲的车后走着,我们要到三里以外的曹家坟那块麦地里装麦子。 我默默走着,大约过了四十分钟,我们才来到我家的麦地。一地的麦个子,像打败了的敌人的尸体一样躺倒着。我父亲的农活在队上是一流的,父亲割出的麦茬子又矮又齐,捆出的麦个子,中间卡,麦穗儿齐齐的,连一个倒穗都没有。 父亲说,你踩车吧。父亲的口气有些缓和,我觉得心里轻松下来。他用铁叉往车上摞,父亲还是那么能干,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让我产生一丝敬意。这几年也确实亏了父亲了,母亲有病,弟弟们一直上学,没有人帮父亲干活儿,全家人的饭碗只有父亲一人担着,他也真够累的了,想到这,我的眼眶热起来。你发什么呆?父亲在车下吼叫起来,我猛地发现我的周围堆了不少的麦个子,我必须尽力把它们放得有条理。父亲的快捷,使我不得不一改往日的劳动习惯,我必须配合父亲,动作慢了,父亲甩上来的麦个子会堆得老高。时间不长,我的体力已不支,就感到我的腰开始疼痛起来,特别难受。我恨不得马上跳下去,逃离现场。太阳一电线杆高了,太阳一出来就烫得要命,我感到浑身灼热,像在蒸笼里劳作。天空没有一片云彩,湛蓝、湛蓝。太阳在天空自由地释放着它的热量,好似要把大地烤出个洞来。很多飞虫躲到树荫里去了,只有燕子在空中飞来飞去,它们不断地吃着从麦地里飞起的小虫。有时它们从我的眼前飞过,我听到了它们飞翔时的快乐声音。站在高处,我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在农村很少有站在高处的机会,此刻我看到我的村庄,没有以前那么好看了,那么整齐有秩序了。到处堆满了新鲜的麦秆。那些老母鸡趁机兴奋起来,在麦根旁不停地啄着残余的麦粒。一段破墙,一座废弃的面粉坊在阳光的照耀下都显得面目丑陋。人们在丑陋的街道上穿行着,扬起的灰尘飞起又落下。 为了早日返回我郑州的建筑工地,我日夜跟着父亲干,没几天我们就把我家的麦子全部收获完。临走的那天早晨,父亲拍着我的肩膀哽咽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本来想只跟母亲说一声,就离开家门。没想到父亲这样让我突然难过,父亲说,拴马,你能不能在近一些的地方打工,你母亲这样了,我也六十多岁的人了,腰又不敢弓。父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脆弱过,今天的样子让我心里难言。我知道我的很多书籍存放在郑州,我只有到了那里才能完成我的作家梦,那里有我的蓝天。我只好撒了一句谎话,我对父亲说,那段工程快完了,结束以后我就要求老板回石家庄的工地。石家庄根本没有那个老板的工地,我这样说只是宽慰父亲。 后来在工地的日夜,我的脑海里时常出现父亲落泪的样子,良心要求我必须回到父母身边。后来我终于把那一堆心爱的书籍丢掉,踏上了回家的列车。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父母。 我家住在村子的最南边,没有院墙遮挡,可以一眼看见田野,看见土地。 我经常坐在我家的窗前读书。累了的时候,一眼就看到田野,看到田里劳作的父母,看到辛勤的乡亲们。无论春夏秋冬,他们总是早出晚归,有时披星戴月。一年一年劳作在土地上。无论社会怎样进步,时代怎样变迁,他们都不改初衷。辛勤地耕耘着,丰收了没有狂喜,歉收了没有恼怒。慢慢地我对他们的劳作感兴趣了,除却读书,大部分时间凝望。 他们劳动起来都非常认真,没有一个虚晃的动作,每一步都是那么踏实。翻地,撒种子,除草,浇水。每项劳动都是认真,完整地去对待。即使我们村庄里老懒走进田里,干起活来,也认真,不出虚力。 凝望他们的劳动,真美。阳光把土地照得干净,鸟儿在他们的周围飞舞。劳动工具就放在他们的身边,上面沾着点滴的泥土。田里有牛,有马,有驴。在主人的驱使下拉犁,耙地,配合得十分默契,累了就站在原地休息一下。主人手里拿着鞭子,但从来不抽打,有时只是象征地摇晃一下。 我一边凝望,一边写日记。这是心灵对土地的反应。 春天,万物复苏,那棵最先绿的草,首先映入窗口。让我看见,让我欣喜,让我感到冬天就要过去了。慢慢地,三棵,五棵,百棵,万棵,数不清了,它们都绿了。点缀着土地,点缀着春天,点缀着农人的企望。它们都有自己的花朵,都有自己的色彩,也有自己的梦想。有风儿时常光顾它们,有蜂儿远道而来做客。对自己的芬芳从来不吝惜,让风儿送到远方,送到人们的鼻孔中。让人感到春天的美妙。 由于长时间的凝望,我成了一个诗人,报纸,杂志,把我用心灵的歌吟刊登出来。我欣喜,欣慰。因为,我把对土地,农人的热爱,用文字表达了出来。 后来我突然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几十年他一刻也不停止劳作的原因。直到有一天我把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上的诗作拿给父亲看时,父亲眼里噙满了泪水。这也许是父亲的心愿,父亲是不轻易掉眼泪的人。他那么倔强,那么顽固。他的情感却倒在了文字面前。 2012年6月19日我正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的作家梦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