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报人、时评作者、商人、译者……金庸的多面人生,和他开创的武侠世界一样精彩。近日,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闲坐说金庸》一书。本书由查氏后裔、与金庸同宗的学者查玉强历时7年撰著而成,以46个主题篇章解码金庸的传奇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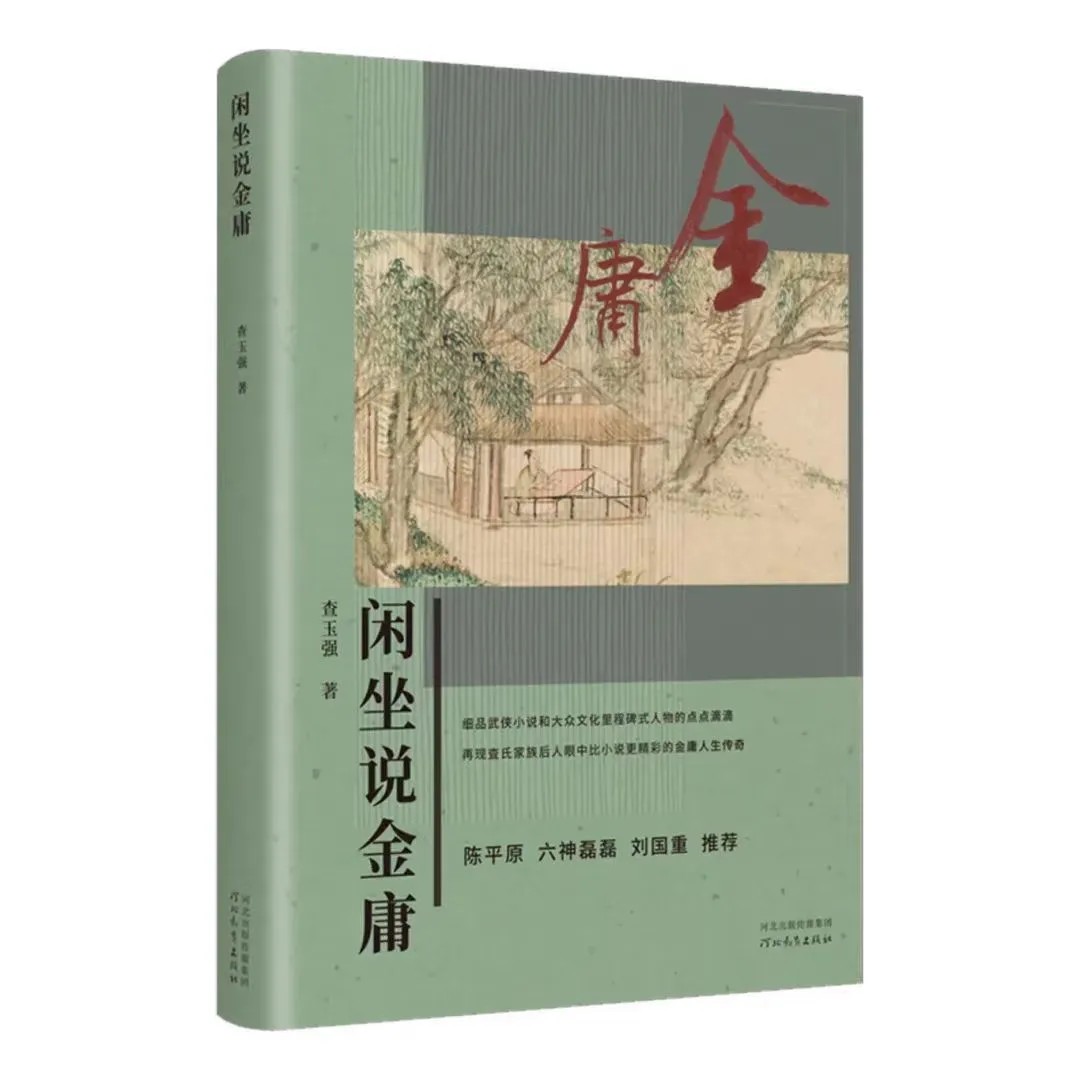
上中学时掘到人生第一桶金
金庸原名查良镛,他的故乡在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作为金庸的同宗后辈,查玉强在书中系统梳理了海宁查氏几百年的发展脉络。海宁查氏为文宦之家,整个家族历来不提倡从商,但是查家又从来不乏经商人才。金庸的祖父查文清在老家袁花镇开办了茧行、丝行、酱园,还开了一家当铺。当时在袁花镇八大姓中,查姓已是独占鳌头,有“袁花镇,查半边”之称。
祖辈的经商基因也流淌在金庸的血液中。在上中学的时候,金庸便独具慧眼,抓住当时小学升初中参考书市场空缺的商机,与两位同学合作编辑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该书在1940年升学考试的节点上由丽水会文书局出版发行,一投放市场,立即受到学子与家长们的欢迎,销售范围很快冲出浙江,覆盖到江西、福建、安徽等省。书局出乎意料地收到大量订单,一时应接不暇,赶紧加印。第二年需求不减,反响仍旧强烈。金庸与两位同学由此赚得不少版税,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多次汇钱接济昔日老友
金庸重情重义。1940年秋冬之交,日本侵略者搞细菌战,当时衢州发生了鼠疫,金庸就读的衢州中学有好多同学染上了鼠疫。但金庸不怕传染,有个姓毛的同学得了鼠疫,他与护工一起把这位同学送到了衢江的隔离船上。

金庸同学余兆文
求学期间,金庸与余兆文、王浩然等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因为金庸去了香港,同学之间数十年没有见过面。1986年,当金庸来到余兆文家,看到好友居住在一间既无厨房又无卫生间的房屋内时,他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我要给你在南京买房子!”余兆文坚决不同意,相互争了一阵子。最后,金庸看到老友始终不松口的样子,考虑到再坚持下去可能会伤及老友的自尊心,于是改变了主意。事后,便多次从香港汇钱以接济老友。
查玉强曾见过1992年6月19日金庸致王浩然的信,在这封充满兄弟情谊的信里,金庸贴心地嘘寒问暖,其真情跃然纸上:“你的居屋要购商品房,如上次所汇之款不敷,请不客气告知,你我情若兄弟,义当相助……虽然大家年届古稀,少年情谊,丝毫不改也。”
曾在湘西当过农场主任
抗战时期,金庸在浙江嘉兴、丽水、衢州以及江西、湖南等地辗转,还曾在湖南省泸溪县湖光农场做过一段时间农场主任。
在湖光农场,金庸负责农场的一些管理工作。在工作之余,金庸除了看书,平日里也经常到农场旁边的香炉岩村与麻溪口村去玩耍,他结交了几位农民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是一位姓覃的朋友。金庸常跟着他一块儿去捕鱼。
当年的金庸,在泸溪村寨,在辛女岩下(即后来武侠小说中写到的铁掌峰),在与村民同娱同乐、尽情交往的过程中,获得了人间真情的滋养,也切身体悟到“侠”与“义”的真谛。同时,他还领略了湘西古老而神秘的地域文化,为日后创作武侠小说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用不同笔名扮演不同角色
1955年,金庸的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报纸上连载,随后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武侠旋风。作为报人,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评论、搞翻译,旁人见之眼花缭乱,而金庸却游刃有余。金庸在写作时,多用笔名,偶尔也用本名查良镛。
“查理”是金庸早期使用的一个笔名,他的中学同学都知道这个笔名。1941年9月,金庸还在读高中期间,就以“查理”的笔名向《东南日报》投稿《一事能狂便少年》,此文当时刊登在由陈向平任主编的“笔垒”副刊第874期上。最具浪漫色彩的是“林欢”这个笔名。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结婚后,曾用“林欢”的笔名写过十几个剧本,这个笔名别有深意:查与杜两个字的部首都有木,“欢”是指他们婚后幸福快乐的生活。“黄爱华”是金庸在《明报》“自由谈”专栏与《明报月刊》所用的笔名,里面蕴含着他对中华之爱。
在《闲坐说金庸》一书中,作者对金庸的20余个笔名进行了分析整理,从而得出结论:“但凡用本名者,都是一些严肃题材,是作者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然其虽有众多笔名,但在签署时也不是信手拈来,而是有所分工、各有用途的。”比如:“金庸”多用于写武侠小说,“徐慧之”专用于写社评与专栏文章,“姚馥兰”是用来写影评、剧本的,“乐宜”则用于翻译文章……他有意地用不同的笔名扮演不同的角色,将文艺创作、评论、政论和翻译等加以区别,通过笔名构建多重文化身份。
当武侠逐渐成为文化符号,《闲坐说金庸》以其温暖的人性视角与严谨的学术态度,为金庸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正如查玉强在本书后记中所说:“冀能为再现真实的金庸,做一点点有用功。”